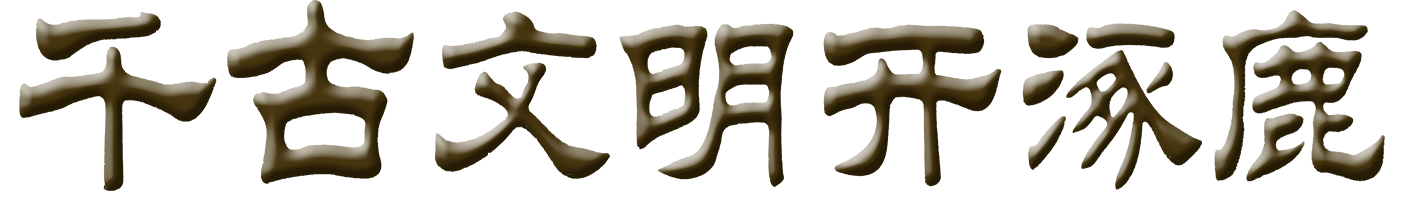“戏窝子”涿鹿
一代名净蔡有山武工、架工俱佳,开打之中眼疾手快,动作干净利落,背扎靠旗、头戴雉鸡翎、腰挂宝剑也能做高难度动作,浑身上下的装饰物不磕、不碰、不挂、不乱,人称“勇猛武生”。有一次,他在沽源演出《打龙袍》,观众达8000人,卖票处的栅栏都被挤坏了。他不仅演技高超,戏德也高尚。他患有严重的疝气,腰间常年缠着带钢丝的腰带。1961年,剧团在沙城新落成的剧场演出《大名府》,他饰演卢俊义,穿着五寸高的靴子从两张桌子摞起来又加了一把椅子的高处做“垛子叉”,落地后,还要四肢跷起来,以肚脐为中心旋转360度,不幸被腰带里的钢丝扎破了肠子,鲜血立刻涌了出来。他强忍疼痛,到后台简单包扎后又返回台前,直到把戏演完,卸了妆才发现肠子被扎穿了。当时的县委书记派车把他送到北京的医院,立即手术,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恐怕就没命了。

涿鹿县老年大学晋剧社在溪源村演出化妆照,左为涿鹿县老年大学晋剧社学员刘爱平,右为涿鹿晋剧张家口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乔润林 拍摄者:霍汉清
涿鹿人“热”戏,几乎村村有戏班儿。
地处涿鹿西山深处的屈庄村只有百十户人家,但很早就成了班儿,以“蹦蹦戏”和二人台为主,行头大都是自制的廉价布衣。当时十里八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,“屈庄戏不用问,一人一根檀木棍”,言其条件简陋。1964年前后,村里出资请来专业师傅,利用农闲时节,排演了整本大戏《六月雪》《乾坤带》《下河东》等,雇木匠、裁缝做了戏服和刀枪剑戟,又发动群众集资为戏班购买服饰。百姓都很清苦,但还是拿出了从牙缝里省出的钱。村民谷永德大冬天连件棉袄都没有,一直穿件山羊皮袄,腰间系条麻绳,却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仅有的七块钱——在当时,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为让人物出彩,演员们一丝不苟,精益求精。四顷梁村的业余剧团1970年正月里去外地演出,冰天雪地,穿河风异常寒冷,演《沙家浜》时,演员一出场,仍然如往常一样,绿裤白布衫,袖口挽到胳膊弯,赢得一片掌声。演员陈建明为了扮好杨子荣,头戴虎皮帽子,外套黑长衫,里面是虎皮背心,靴子的脚面箍着虎皮罩面。其实这些装饰都是他用双层牛皮纸做的,他用红黑颜料勾出虎皮的斑斓花纹,用烟盒的锡箔纸点缀其间,煤气灯一照,闪闪发光,极为引人注目。散戏后,几个老大爷非要上台看看这是一件什么“宝衣”,看后大笑不止,连连夸他:“真有你的!”
那时候,戏班到外村演出时并不约定吃饭与报酬,由大队分到各家各户,村民都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戏班,吃得好的有炸糕、莜面,最次的也是小米豆饭。演出结束之后,有管饭任务的人家来到台下,这个喊:“我家两个!”那个喊:“我家三个!”有的直接点名:“我要杨子荣!我要铁梅!”
上世纪90年代的涿鹿,戏曲进入低谷,除了个别村镇庙会期间邀请外地剧团唱几场山西梆子,其余时候就是老人去世后请鼓匠班子唱几天坐场戏。老人活的时候看不上戏,去世了,怎么也得让老人听着熟悉的山西梆子驾鹤西游,无论穷还是富,都要唱几天坐戏,否则就是不孝。那时人们在家里不敢大声唱山西梆子,也不敢播放山西梆子,怕被说是家里死了人,山西梆子在涿鹿沦为了“丧葬文化”。但山西梆子在老百姓心中根深难移,不敢大声唱就小声哼,就小音量播放。
唱戏离不开戏台。涿鹿县明清时期的戏台都是与寺庙连在一起的,是寺庙的组成部分,故也称为“庙台”;又因与音乐戏曲有关,也称“戏楼”“乐楼”。新建的戏台使用前有一个仪式叫“轰台”,也叫“打台”“镇台”“祭台”等,有“文轰”“武轰”。选个良辰吉日,在台上杀掉一只公鸡,鸡头挂到台子的大梁上,然后放鞭放炮,这是“文轰”;“武轰”要上锣鼓,由花脸演员手执兵器,口中念念有词在台上转几遭,然后杀鸡,鸡血洒在台子四周,点燃黄表纸,把鸡头挂在大梁之上,鸣放鞭炮。
爱戏的人都知道,好多戏是让人分辨忠与奸、善与恶、美与丑、好与坏的:《打金枝》里唐代宗礼贤下士,郭子仪居功不傲;《黄沙岭》内纣王荒淫无道;《明公断》中陈世美贪恋富贵终致身首异处,包拯刚正不阿世所共仰……一部戏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,更映衬着一个家一个国的兴亡衰败。演的是大千世界,传的是生存智慧。
千里桑干,文汇涿鹿,繁华逝去,更见真淳。戏曲的魅力无法阻挡,一旦入门,便终生难以放下。喜欢一样东西有时候得赶到一个“点”上,这个“点”就是触动,就是越过门槛的那一瞬。也许哪一天,那些喜欢劲歌热舞的年轻人受到触动,会突然痴爱戏曲。如今文化虽然多样,但戏曲毕竟是多少代人打磨过的好东西,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,始终有人无怨无悔地坚守弘扬。只要传承得法,耐心等待,戏曲的美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。
来源:《文艺报》2023年12月13日第8版